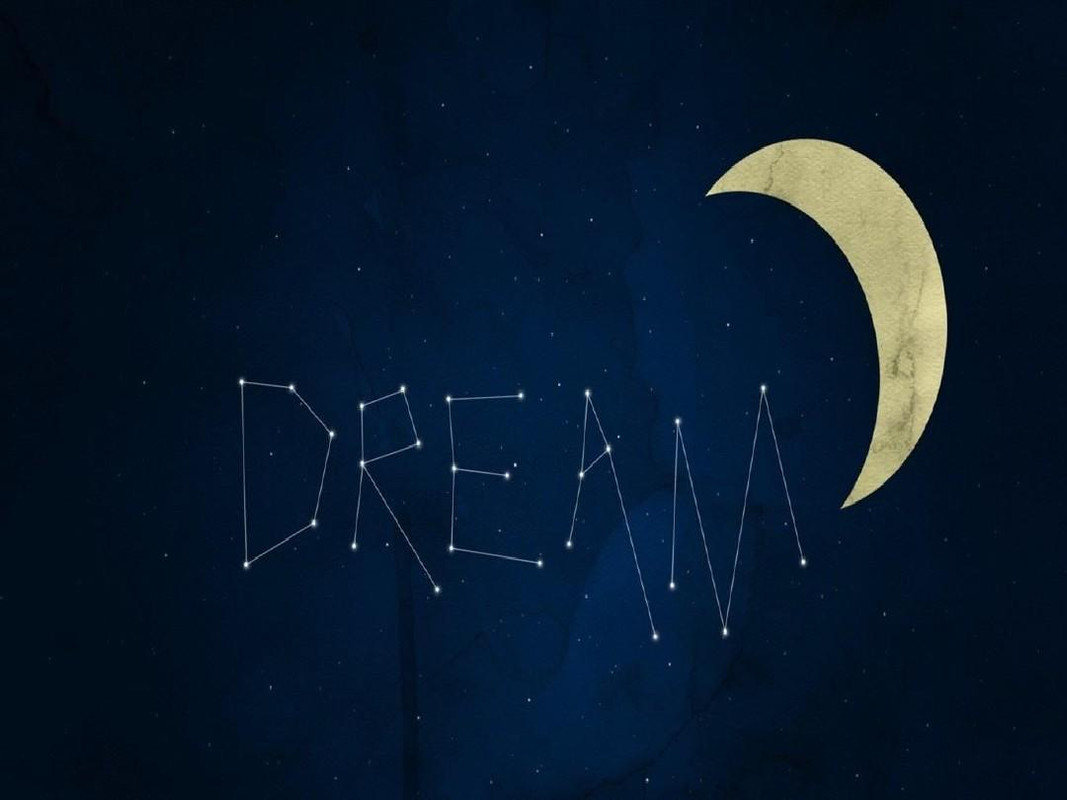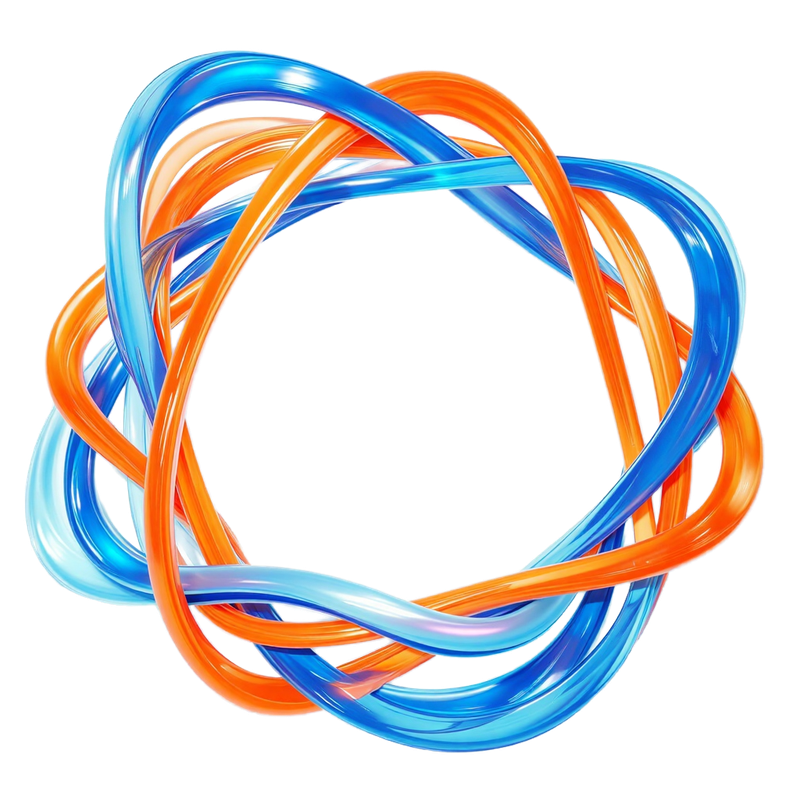偏爱-主体性的让渡与凝视价值的重构

明天就走了,后面的更新博客可能没这么频繁了,今天想写一点我一直想表达的,这也是我自身很大的矛盾点的具象体现:感性 和 理性 的矛盾体。
今天想聊的话题是偏爱,关于这个词,其实我一点认知都没有,聊到偏爱,只会反应到仙剑奇侠传里的插曲《偏爱》。但后续的生活种,我从前任的口中听到了偏爱的需求,可以理解到对方对种情感需求的极度渴望。关于“偏爱”,就是在那个时候,我有了很多的思考,但是这些思考也没有分享出去,因为想与做其实很难一致,也就是我一开始提到的,我是一个感性和理性的矛盾体。
当然,这次写关于偏爱这个话题,我更多的是想从思辨的角度去聊,这也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,虽然和实际做法矛盾冲突,原因已经解释过了。
关于偏爱,其实是个悖论
萨特在《存在与虚无》中早已预见现代爱情的悖论:**我们既渴望成为爱人世界中的绝对中心,又恐惧于完全消融在对方的主体性中。**这种矛盾不是个别现象,而是人类关系中的普遍困境,它不断在现代亲密关系中重现:我们既希望伴侣因我们而改变,又害怕他们失去自我;既渴望被全然爱慕,又担忧成为对方生活中的可替换零件。
关于原则
原则性强的人之所以在爱情中显得”曲高和寡”,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框架构成了一种不可让渡的主体性堡垒。当一个人说”即使是你,我也不会放弃原则”时,他实际上在捍卫自我存在的边界。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愈发明显——我们推崇个性与独立,却又在亲密关系中隐秘地期待对方为自己破例。社交媒体上”浪子回头”的故事总能获得大量点赞,正是因为这种戏剧性的主体性让渡满足了我们对”独一无二被爱”的幻想。但这种幻想本身包含着一种危险的逻辑:爱被简化为一种自我重要性的证明,而非两个完整人格的相遇。
萨特和波伏娃的关系正是这种矛盾的典型案例。萨特坚持”人是自由的”这一存在主义核心观点,认为即使在最受限的环境中,人依然保有选择的自由。而波伏娃则尖锐地质疑:”一个被关在闺房里的女性能够超越什么?”——她指出了理论上的自由与现实中选择权的根本区别。这种哲学分歧也反映在他们的爱情契约中:表面上的绝对自由关系,实则充满了嫉妒与占有的暗流。
凝视的双重性:确认与侵犯
凝视的辩证法在这里发挥着微妙作用。萨特指出,人类既恐惧被客体化,又依赖他人的凝视来确认自身存在。在亲密关系中,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尖锐。当伴侣质疑”你对任何人都一样好”时,真正恐惧的不是善意本身,而是自己未能成为那个能够改变你行为模式的特殊存在。她/他渴望在你的眼中看到自己引发的独特反射,这种反射构成了她/他主体性的一部分。
但问题在于,如果这种改变过于彻底,如果一方完全让渡了主体性,那么关系中的凝视结构就会崩塌——没有人愿意爱上一个完全失去自我的影子。正如萨特所描述的咖啡馆侍者,当他完全认同自己的职业角色时,他就失去了作为人的主体性,变成了一个”自欺”的存在。在爱情中同样如此:过度让渡主体性的一方最终会失去吸引对方凝视的能力,因为凝视需要差异与对抗才能持续。
困境与出路
现代爱情的神话总是承诺”找到那个让你完整的人”,但更健康的视角或许是”找到那个让你更完整地成为自己的人”。挪威哲学家拉斯·史文德森在《爱情哲学》中指出,当代人将爱情宗教化,期待它解决存在的孤独问题,这种过度期待恰恰导致了关系的失败。真正可持续的爱情不是主体性的单向让渡,而是一种相互的”主体间性”——两个完整的世界相遇,各自有所调整却不丧失核心。就像两棵相邻的树,根系交织却各自向上生长,共享阳光却不争夺空间。
萨特与波伏娃的关系虽然标榜自由,实则充满了控制的暗流。萨特可以坦然向波伏娃讲述自己的艳遇,但当波伏娃的美国情人奥尔格林向她求婚时,萨特却”嫉妒得发狂”。这种双重标准揭示了所谓”自由关系”中的权力不对等:谁的自由被保护,谁的自由被限制,往往反映了关系中更深层的权力结构。
关于偏爱的回答
具体而言,或许可以这样回应:”我的道德让我对所有人都保持基本善意,但我的选择让你成为唯一分享我生命细节的人。“这种回应既承认了普遍性原则的存在,又肯定了关系的特殊性。它暗示爱不是通过例外主义证明的,而是通过持续的共同建构实现的。荷兰心理学家约翰·赫尔曼斯的研究表明,最稳定的长期关系往往不是那些充满戏剧性情节点缀的,而是双方能够将彼此纳入自我叙事而不丧失自我连续性的。
爱情的持久魔力恰恰在于这种微妙的平衡——足够的主体性让渡以创造亲密,足够的主体性保留以维持吸引。我们既不是完全独立的孤岛,也不是融合成一体的混沌,而是在潮起潮落间始终保持适当距离的两片海岸。也许,理想的爱情不在于让对方为我们打破多少原则,而在于我们共同发现了哪些值得共建的新原则。在这种共建中,我们既确认了自己的存在,也见证了对方的成长,而凝视——这种人类存在的基本需求——就在这样动态的平衡中获得了它最美好的实现形式。
待更新……